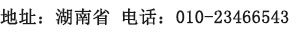我为何爱吃桶底饼和硬壳饼
文/郑钟海
我算是比较爱吃甜食的人,但这口味基本都锁定在甲子所的“甜系列”上,比如甜丸、甜面、甜糜,又比如糕点、饼类。孥仔时,酷爱吃,现如今,虽说胃口不可同日而语,但还是能吃一些,特别是到了清明前后,我念兹在兹,尤爱吃两种饼:桶底饼和硬壳饼。
同学许伟争曾写过有关这两种饼的文章,我读了受益匪浅,解开了多年来不解之题;伟争家是做饼的,据他所说,他爷爷那一辈在甲子所特别有名,不仅是一有名的饼工匠,还是一有文化的饼工匠。故而,他爷爷能把甲子所饼类的前世今生、追本溯源说和写得一清二楚,而伟争从小耳濡目染,对饼类的发轫自是了解颇深,所写的依据、旁证应该也有一定的说服力。至少伟争能说服了我。
甲子所的清明饼多达十几种,但我独钟这两种,时至今日,我也说不上具体的缘由,若硬要找出个子丑寅卯的话,我想应该归于小时候那次的“好食”;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。
我老觉得我们80后生长在相对而言物件比较匮乏的年代,但很幸运的是,那时候能吃的似乎都无害,最好看的也是最好吃的,压根不存在货不对板,也很少听说无奸不成商;生意可以是小本买卖,但绝对是良心营业。所以,小学门口、老街窄巷、庙前寺后,只要看到有摆摊的,基本都会围拢上去,摸着干瘪的口袋,未必会买,但肯定会吞一吞口水。
读小学时,记得我有几个姓许的同学,比如许汉奕、许汉典、许克,好像都是居住在灰路那里;那时每每路过灰路,那几间饼铺像是有魔法似的,毫不费劲就能把我那一双小脚给缠住,随之一双贪婪的小眼直勾勾地盯着饼铺所摆着的物件不放。刚出炉的饼类,热腾腾、香喷喷,你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馋嘴,那简直就是在使坏;你不知道唐僧会来,可能还不会惦记唐僧肉,他都来到你跟前了,你还不食指大动、撑开血盆大口,鬼才信你呢。
后来有一次,跟着汉奕他们去了他们家,印象中,走的路是小巷,七拐八弯,入了正门;坐下来后,我总会闻到浓郁的饼香,就是那种刚刚从烤炉拿出、仍在腾发着热气的饼香。当时我是如何挣扎的,我现在毫无印象了,倒是有不灭记忆的是,也不知是待客之道而为还是看出了我的小心思,汉奕他们出去个几分钟,居然能把勾我灵魂的饼给拿来;接过手时,饼还是烫的,且软乎乎,上面还撒了一层粉。
后来我才知道,这就是桶底饼;桶底饼,因其状如古代木桶底而得名,真名叫米饼、粉饼。世间事往往就是如此好玩有趣,本名未必入人心,花名却早已路人皆知。我爱吃桶底饼,除了它软而不粘,饼面厚薄有致,更重要的是裹着那层粉一起吃下后,舌尖上、齿颊处、喉咙中,总会有一股淡淡的甘甜。回甘之余,又忍不住再吃一块。读了伟争那篇文章后,我才茅塞顿开:原来桶底饼里面含有赤菜成分,这种赤菜价格不菲,且有清热解毒、润肠通便之功效。据说,在古代,甲子所城的孥仔“做阿娘”(出痘),就会吃这种桶底饼,可以大大缓解病情。
再接前文;当时,我刚吃完桶底饼,汉奕他们又冷不丁地拿来香馥馥、热烘烘的另一张饼来,这便是硬壳饼。后来,我才知道原来汉奕他们家是做饼的,而且就是灰路那几家能勾住我灵魂的饼铺;前面开铺,后面居家,潮汕典型的商住一体。顾不上烫嘴和热气,我也毫不留情地消灭了那饼;多年以后,每次吃到饼类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次在汉奕他们家吃过的饼。人大了以后,好多记忆或许找不到出处,但有些记忆却如胎记,始终钉在那里;那里就叫小时候。
据伟争说,硬壳饼又叫红花饼——饼的中央戳着一红花印,故而得名,其实它正名叫龙文饼,原来这饼是清代由福建龙文县(现为漳州市龙文区)传入甲子所城,这便是典型的因地而名,也算是不忘本之由。阁下不知有无发觉到:硬壳饼除了印有大红花,另一面还有一孔,像一肚脐眼,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肚脐饼。每每吃这饼,我会想为何要戳这么一孔呢?伟争只写了会在“送入烤炉烘焙前,用筷子在饼的背面戳个孔”,却并无给出答案,我就瞎想一下:会不会是考虑到热胀冷缩,戳个孔便于散热散气,如此才不会把饼的圆状给撑坏了,就像火车轨道那样,之间会留有缝隙,才不会相互挤轧,造成扭曲或向上拱起。
时至今日,我还是爱吃桶底饼和硬壳饼,说来也吊诡,有时味蕾也会像照片那样被定格的,或许以后吃到的肯定比以前的要好吃百倍,但那种满足感、幸福感却永远不如以前所吃到的。我总认为,这里面还糅合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,这便是人情味。
注:感谢许伟争同学提供相关资料和照片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